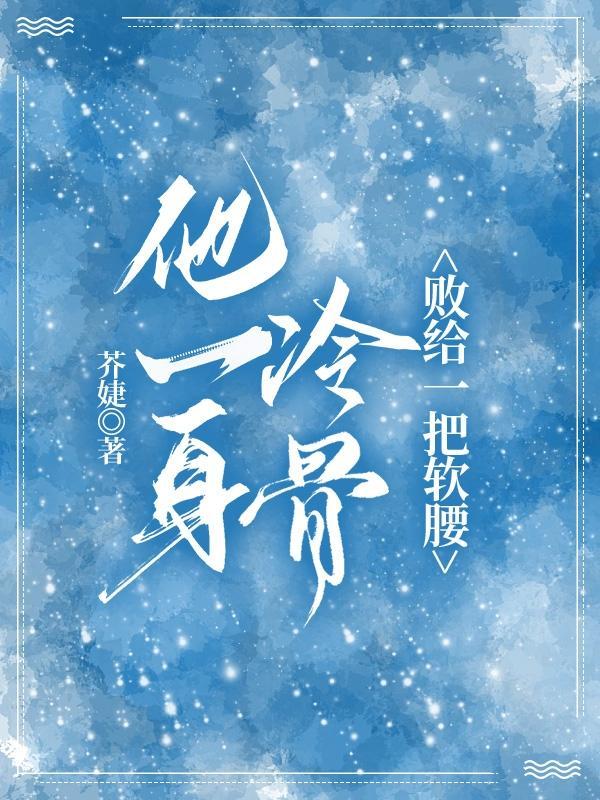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十七章(第3页)
社员们跟着副队长李丁民乱糟糟地向河滩里去了,吴根才站在皂角树下没动,等月儿走到跟前,他把月儿叫住。和月儿相跟在一起的巧红听见队长叫就也站住脚。
因为巧红,虎堆虎林两兄弟和郭安屯大大地闹了一场,但是虎堆已经管不下巧红了。只要一有机会巧红就偷偷摸摸地要和郭安屯好一回,巧红觉得干那种事郭安屯就是比虎堆强。为这事巧红没有少挨虎堆的打。和郭安屯偷偷摸摸干那事也罢,让虎堆一顿顿饱打也罢,巧红和月儿的好却没有断,两个人来来去去的总爱相跟在一起。刚才往坡道下走的时候,巧红就不经意地说了月儿一句,她嫌月儿走的慢,就说:“月儿姐,你今天这是咋那,走两步路也怪模怪样的,像是得了痔疮一样,咋那个走法呀?”当下把月儿吓了一跳。到了皂角树下月儿的脸无缘无故地就红了,别人谁都没有在意,但是跟在月儿身边的巧红却翻动起心思。因为跟前人多,她没好意思问出口。现在队长把月儿叫住,她就现月儿的脸比刚才红的更厉害,连白嫩嫩的两颗耳垂儿都樱桃般的染上红色。巧红哧哧笑着正想说一句逗弄人的话,却被队长给打走了。吴根才对伴着月儿不走的巧红说:“翻你的地去,这没你的事。”巧红狸猫似的花眼闪动几下,噘翘着嘴不高兴地走了。巧红在往河口里走时回头再张望几下,看见队长凑在月儿脸前正说着什么,她就敏感地想到去年郭安屯派她去上河滩看谷子时的情景,就奇思妙想起来。巧红别的窍门不开,但对这一窍却开的很,她马上就猜想出来月儿是和队长好上了。
巧红走开后,吴根才脸上带着关切的笑容对月儿说:“你就不去翻地了,你到场上的库房里挑选麦种去吧。”这是吴根才第一次在派活的时候照顾月儿,原来他虽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却一直没有特意关照过月儿,他害怕闹出闲话。但是有了夜黑间的事情,他就没有理由再不关照她了。
月儿下面肿胀的有些难受,正愁今天不好往黑熬,却得到了吴根才的关照,给她派下一件这么好的轻松活儿。月儿心里酸酸的涌起一股复杂的感动,是负出沉重代价后获得一点疼爱的那种痛心的感动。派来挑麦种的还有一个马桂花,把马桂花也派来挑选麦种,吴根才不是在看郭安屯的面子,他是真的同情她是一个寡妇。
郭安屯当上政治队长后几乎再没干过一整晌活,干上半晌他就总要到别处去溜溜哒哒半晌,说是到别处查看,实际上是借机偷懒。他到了地里才翻了几锨地,就把钢锨插在地头上,背起双手又到别处查看去了。他今天心里真的不瓷实,上工的时候他看见吴根才把月儿给叫住了,当时他当然不能跑过去问吴根才叫住月儿是要干啥。现在翻地的人群里没有月儿的影子,那吴根才肯定就另给她派下活了。他不知道吴根才安排月儿干啥去了,他想探个究竟明白,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这好像是吴根才第一回单另安排月儿去干别的活。
在别的几块地里,也都不见月儿的影子,郭安屯就更感到纳闷,他就顺道从河口里上来进了村。一走到皂角树下,他就看见月儿正盘腿坐在库房门前的平场上怀里抱着一个小竹筛低头挑选麦种,尽管月儿旁边还坐着他的老相好马桂花,他的心还是咯咯蹬蹬了好几下。吴根才怎么能安排她来干这种活,她是大地主的女儿,是地主儿子的媳妇,是劳动改造被管制的对象,怎么能让她这样舒舒服服地大腿压小腿坐在凉凉的树荫底下挑选麦种,而那些贫下中农的女人们此时此刻正在大日头底下挥舞着钢锨红汗黑流地翻地呢。他真想过去把低下头静静挑选麦种的月儿赶到河滩去翻地,但他终于还是没有那样做。月儿来挑选麦种是吴根才安排下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吴根才的面子他不能不买。
郭安屯从河口里上来,就让月儿看见了,她吓的把脸低垂下去不敢再往起抬,生怕把他招惹过来找麻烦。马桂花和月儿不一样,她倒是期望着郭安屯能过来,他们有一阵子没有在一起了,她还真有点想他。马桂花停住手里的活,扬起脸直往从沟口里上来的郭安屯脸上看。郭安屯犹犹豫豫着正要往过走,这时候场子那边的教室的窑门开了,学生娃像是散了的羊群,哇哇叫着从教室里跑出来。郭安屯眼尖,他一眼就瞅见下课出来的学生中间还加杂着地主的儿子。新生现在已接替父亲也被人们叫成地主的儿子,但是耀先并没有因为新生的接替就从中解脱出来,他还一如继往地被叫成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儿子是他们两代人的共同名称,不知道若干年后新生再有了儿子,会不会也被人们叫成地主的儿子,如果真要是那样,就不仅仅只是他们一家人的悲哀了。
郭安屯在下课的学生中间看见了新生低矮瘦小的身影,不由地一愣,然后就疾步向教室走去。当他从皇甫老师嘴里得知是吴根才今天早上亲自把新生送进学校时,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也就有了几分懊丧,就觉得自己费心摆好的算盘却让吴根才噼噼叭叭地拨动响了,自己为他人做了一身嫁衣裳。
晌午间快要下工的时候,河渠上跑过来一个外村的年轻人,年轻人跑过来站在地脚头扯开嗓子直喊虎林虎堆,说是歇马庄他姑家的窑塌咧,还伤了人。虎林虎堆兄弟俩一听这消息,撂下钢锨踩着才翻开的松软的虚土,就急急地往歇马庄去了。姑家出了塌窑伤人的大事,他们能不着急。这事搁谁身上都急。他们这个姑,小时候像亲娘一样待他们哥俩,兄弟俩生怕姑有个三长两短。
摆溜溜翻地的人们乘势拄着钢锨把活儿都停歇下来。挥舞着钢锨翻地确实是一项很苦重的活儿,快到下工的这段时间人也就累的差不多了。吴根才见出了这事,再看看社员们东倒西歪的也没了朝气,就抬起头看天上的日头影儿。那时候的队长们掌握劳动时间,不是看手腕上的表,他们手腕上那里有那东西,他们的表就是悬挂在头顶上的大日头。日头照下来的影儿斜了正了就是他们上工下工的时间,他们辈辈数数都是照着日头影儿安排作息时间的。
吴根才看看天上的日头,再看看照在地上的人影,抹下包在头上的羊肚手巾顺势擦一把脸上的尘土和汗渍,亮着嗓子喊一声:“下工。”
早在他抬起头往天上看日头的时候,社员们就等着他喊这句话哩。吴根才的话刚出口,社员们就哗啦一下散开,争前恐后地往河渠上走,争前恐后地往家走。下工往回走的劲头远比上工往地里来的劲头大。吴根才没奈何地摇头笑笑,也迈着急骤的步子,随在拧成一股绳的社员身后,向村里奔去。
虎堆不在下工的人群里,巧红就闪着狸猫一样的花眼朝后看,当她看见郭安屯拖拖拉拉地走在最后时,她就有意慢下来。
郭安屯今天慢慢腾腾地走在最后,不是因为鞋烂跟不上脚走不快,他今天穿在脚上的鞋半新不旧的还看的过眼。他走的慢,提不起精神,是因为心里有了一档子事,就是月儿去挑选麦种和月儿的儿子上学的事。他在琢磨着这里面的原因,在想着应对的办法。
下工的人群风快地就在河渠上走远了,郭安屯看见前面就剩下一个巧红,还不住地往回扭着脸看,就知道她是在等他。虎堆开枪砸窗把事情闹明之后,很让郭安屯难堪了一阵子,那一阵他尽量避着不再碰虎堆的面,可巧红不忘旧情时不时地用狸猫一样的花眼挑逗他,后来他们又偷偷摸摸地好了几次。郭安屯紧走几步追上前面的巧红。
巧红看见郭安屯追上来就侧过脸妩媚地一笑,悄声说:“后晌间我在窑里等你。”说完就追着前面的人群快快地走了。
郭安屯咚咚一阵心跳,惊喜的不行。喜的是这个雪蛋儿一样的巧红又想他了。惊的是她让他再到她窑里去,那地方还能去吗,万一二杆子虎堆闯回来咋办?去年的教训还小吗,那凄厉的两声枪响让他啥时候想起都害怕。
巧红真胆大,敢在大天白日把郭安屯往窑里约。巧红想过了,虎堆他姑家出了塌窑伤人的大事情,把虎堆虎林兄弟俩从地里叫走了,他们肯定一时半会回不来,塌窑伤人是大事,虎堆即是回来,估计也到天黑了。这长长的一后晌不是一个美美的好机会。巧红总是嫌自己的男人虎堆弄那事没有郭安屯本事大,他进去几下就不行了,人家郭安屯就不一样,人家一插进去就是大半天,那个美呀。
匆匆吃过晌午饭,巧红就心急火燎地倚在门上等郭安屯上来,为干那事她决定后晌不上工了。
郭安屯迟迟为为好半天就是不敢往巧红的窑里去,直到上工的钟声响过,社员们上工去了地里,村子里宁宁静静没有了闲杂走动的人影,他才贼一样溜进巧红的窑门。一见郭安屯进了窑门,巧红就往炕上滚。郭安屯却心虚气短的不敢上炕,他想把巧红引到别处去弄事情,那怕是在村背后的草滩石头旮旯里都比在这炕上强,万一正弄到性上再让虎堆堵住,那可就完了。
巧红已经脱得光溜溜的仰面朝天躺在炕上了。“快上呀,还傻愣着站在地上看啥哩。”炕上的巧红踢着腿催促起来。郭安屯再看看已经闩插死的窑门还是不放心地说:“好我的姑奶奶,你就不怕万一……”巧红猛猛地坐起来,两只饱满丰腴的奶子像两只受了惊吓的白鸽子,在她胸前扑扑闪闪的要飞走的样子。巧红眼里露出一丝儿不悦,噘翘着嘴嗔怨地说:“高高大大的一个男人,咋就长了一个老鼠胆,你要是再磨蹭,他可就真的要回来了。快上来吧,他姑家窑塌了,你想他能马上回来。”想想也是,郭安屯这才急急地爬上去……
干完事情后,两个人在一起又缠绵了一阵,郭安屯看着这个钻滚在怀里的雪蛋儿一样白美的女人,有些想不明白,去年他们在一起偷情,是因为她男人不在跟前,现在虎堆黑天白日的都守在跟前,她咋就还想着他?就想问明白这是咋回事。巧红花狐子一样在他怀里倚偎的更紧,然后才不知羞耻地说:“人家想和你好。他光是图个趟数多,一黑夜上上下下的好几回,每回都是三五下就泥一样软出溜了。你一下就顶他几十下。”
郭安屯把巧红的光身子抱在怀里呵呵地乐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虎堆威威武武的一个壮小伙,却是一个在女人身上没本事的瓜瓜蛋。从这之后郭安屯就再也看不起吴虎堆了,连自己的女人都弄不好,还算是个什么男人。
巧红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头从郭安屯的胳膊弯里钻出来,惊惊乍乍地说:“哎,我今天可是现了一个大秘密。”“啥秘密?”郭安屯不经心地问一声。没城府的巧红一下就把自己所谓的大秘密说透出来:“你肯定猜想不到,月儿和队长吴根才好上了,他们就和咱们现在一样,也是这种关系。”郭安屯一惊,扳住巧红光溜溜的肩膀问:“你咋知道的?”巧红嘻嘻一笑又往他怀里钻钻,就把今天她见到想到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总结道:“夜黑间他们肯定在一起弄这种事情了,肯定还弄的挺厉害,不然今天一大早月儿就不会腿旮旯夹了东西似的那个样走路,不会一见吴根才就脸红,吴根才也不会专门安排让她去挑选麦种。”巧红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女人特有的直觉竟然丝毫不差地分析出月儿和吴根才之间已经有了的关系。
郭安屯心里的疑团让巧红点破,但是他不想让巧红看到自己在这方面表现的蠢笨,就故意散淡地说:“你才知道呀。”
这下就轮着巧红惊讶了,她抬起光肩膀,把狸猫一样的花眼睁动的叭叭响,问:“你早知道呀?他们就是有这种事情?”
郭安屯弯曲着手指弹逗一下巧红胸前跳闪的奶子,嘻嘻笑着说:“那当然。”
巧红就痴痴地想:看似安分守己的月儿原来也和自己一样,回头一定要好好逗弄逗弄她不可。
有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有了第二回,就可能有无数回。最后一块回茬地的麦子种完后,月儿和一群女社员腰里系着包袱在地里摘棉花,吴根才过来见月儿跟前没人,就悄声说:“今黑夜,我还在水磨房等你。”月儿一阵心跳,脸就又苹果一样地红了。吴根才说过这话就闪过去走了,月儿却紧张起来,她抬头向四下偷偷地张望一下,四周围的女人都弓弯着腰在垄里摘棉花,谁都没有注意队长从她脸前过去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月儿虚虚地出口气庆幸巧红今天没有跟在身边,往常巧红总是屁股虫似地沾在身边,拉长拽短的咋难听的话都能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巧红今天是到歇马庄埋人去了,那天虎堆他姑家窑塌还真是把他姑给压死在窑里了,今天埋,虎堆一家全都穿白戴孝哭牺惶去了。要是巧红今天跟在身边的话,月儿不敢想象会出现什么事情。
那天黑夜在水磨房和吴根才有了事情后,月儿的心就一直静不下来,就不敢再和吴根才照面,一照见他的影子就心跳,就脸红。但是那天晚上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上天入地要死要活的感觉。是一种既让她害怕,又让她痴迷;既让她想逃脱,又让她想沉入;既让她想抗争,又让她想依附的奇奇怪怪的感觉。
月儿想不到吴根才会过来撂下一句这样的话,接下来她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脑子里空空的乱乱的没有一点头绪,没有一点思维。
那天在水磨房里躺下是为了儿子长长远远的一生,是为了让新生上学,是为了报答九泉之下的小河哥。今天再去是为了什么?对那天的事,耀先至今没有开口问一个字,难道他不知道是生了什么事情?知道,他清楚地知道是生什么事情了。他只是不说而已,他把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屈辱,更深地埋在心里不往外说,他半夜半夜地躺在炕上睡不着觉,连声不断地哀叹,就是这痛这苦这屈这辱在深深地折磨着他呀……
月儿一向灵巧的双手在棉花枝条上颤颤抖抖地揪拽不住一簇簇盛开的棉花朵儿,别的人早采摘到前面去了,她却还远远地落在后面,别人腰里的棉花包袱像怀孕十个月的大肚子女人,高高鼓鼓地都挺撅起来,而她腰里的棉花包袱就和她没有怀养过孩子的肚子一样平平扁扁的。
一晌过去了,又一晌过去了。后晌的日头眼看就要压到西边的山顶上去了,可月儿的脑子里还是空空乱乱的,她害怕天黑,却又盼望着天黑。她有了一种想逃脱又想就范,想挣扎又想沉入,既害怕又期待,既痛苦又兴奋的复杂情绪。
月儿今天一天摘回来的棉花,还不及往日一晌的多。今天她站在棉花地垄里尽想着天黑后要不要去水磨房的事情,那还再有心思采摘棉花。
日头终于落到西山后面去了,月儿把摘下的棉花交到库房顺着坡道往崖口上走的时候,忍不住回过头朝矗立在河岔上的水磨房看了几眼,浓浓的暮色已经缭绕起来,水磨房此刻笼罩在一片雾霭当中,影影绰绰的,她不知道那里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在做晌午饭的时候耀先就看出月儿神情恍恍惚惚的不对头,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她就把擀好的面下进去,结果让一家人吃了一顿糊糊饭。当时耀先看着月儿一脸心神不宁的表情,想开口问一句,但最后还是没有开口。那天晚上月儿走下崖口,回来后他就再没有主动地问过月儿。她不说,他就不问,问什么呢?这些年耀先是被管制的胆小了,但并没有因为被管制而变憨变傻,相反他还更敏感了。他知道月儿下去干啥去了,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时候她能干啥?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他只能咬着牙默默地忍受,心里有再大的悲苦,再大的委屈,再大的愤怒,也只能默默地忍在心里。面对这样凶恶的势力,他只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蚂蚁怎么敢去撼动大树?只要不被人一脚踩死,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算了。
天黑回到窑里月儿又忘了做饭,只是一阵阵坐在炕沿上呆愣。打地埝,干了一天重活回来的耀先看着月儿这样也不忍心再让她做饭,他就自己动手烧火做饭。耀先把米汤烧好,把馍馏热,再剥褪几苗生葱,招呼放学回来的新生和月儿过来吃饭。新生过去坐在小饭桌旁了,月儿却还坐在炕沿上不动。耀先就给她端过去一碗米汤,再送过去一个馏热的二面馍。
耀先和新生坐在小饭桌旁吃完饭,过来,月儿只咬了几口馍,碗里的米汤也只是浅浅地喝了几口。耀先把眼墙上的小灯盏点亮,看着月儿一脸迟呆疑重的表情,就想到一种可能,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再也不能沉默着不说话了,他知道月儿心里可能比他还痛苦。他低声地问:“是不是又……”
月儿没有把头抬扬起来,但她也没有隐瞒,她颤着声低低地说:“是,他又要让到水磨房去。”说完月儿才把脸扬起来,她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和她的心境一样,但是她想听他一句话,如果这时候耀先挺起胸堂硬硬地说一声:不!也许她的心绪就再不复杂了。他们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崖口上熬过了那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她想听他一句话。
耀先把瘦削的刻满了痛苦的脸扬起来,强忍着不让伤心悲愤的泪水流涌出来。这样的结果他早就想到了,即然有了一次,就会有二次,这么好的女人,谁肯只要一次。耀先嗓子眼里堵塞了烂棉花套子一样,他喊不出月儿正在期待着的那个:不。
美丽,善良的月儿跟上他受尽了苦难,受尽了屈辱,受尽了折磨,连一天幸福的日子都没有过,连最起码的男欢女悦都没有过。月儿呀月儿,月儿不应该跟上他经受这没有尽头的苦和难。美丽的月儿应该享受到人世间最最美好的幸福,他给不了她,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寻找吧。解脱出去一个是一个。耀先没有吼说出:不,却低哀哀地说出一句与本意完全相反的话:“你,去吧。”
月儿期待着耀先说出来的是“不”,可是他却说出“去”。如果耀先说出的是“不”,她就会服从他的意志,就会和他一起厮守在这孤孤的崖口上。可是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月儿就更没有了主意。她木呆呆地看着他;他也木呆呆地看着她。他们分别在对方的脸上,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可怕的陌生的东西。
重生后,我宠上反派疯批大佬
京州活阎王裴西宴性格偏执,手段残暴,令人指。前世,池嫣最怕的是,这个男人用那双沾满过鲜血的手,抚摸她细白娇嫩的身体。池嫣这一生,曾无数次后悔与这个男人产生交集,可是直到死后,她才看清楚一切。他替她手刃仇人,用他这条命给她陪葬。池嫣这才知道,这个男人偏执入骨的爱从来都不是枷锁。一朝重生,池嫣先制人。深夜,她穿着他重生后,我宠上反派疯批大佬...
他一身冷骨,败给一把软腰
(双豪门先婚后爱强强联手,白切黑女主vs忠犬型霸总)传闻南家三小姐携肚逼婚,傅二爷不甘被拿捏,打着去母留子的主意。殊不知,南三小姐也是一样的想法。满身锋芒,眉骨里写着冷硬的傅二爷带人杀上门。南笙一把细腰,纤若春柳,穿着素色旗袍,笑意温婉,二爷,这婚,你结吗?傅二爷结!后来,傅二爷求了一枚平安福他一身冷骨,败给一把软腰...
重生:我用虫巢杀穿星空
前世天尊之身。重生后,他建立万界星球联盟,权倾天下。杀伐果断,斩敌百万!谁敢挡我,杀无赦!!除了杀,还是杀!!仇敌?吞噬,化作我的养料!!外星种族?异世邪怪?通通给我杀掉!!杀出一个堂皇大道来!!重生我用虫巢杀穿星空...
那年我双手插兜,修仙后没有对手
唐无忧穿到一本修仙文里,刚传来就要成了妖兽的口中餐。好在能半妖大师兄,魂穿二师兄把她给救回去。正要努力修炼的她现,这身体里还有个魔族圣女,这?她强势回到唐家报仇。魔族圣女报仇?直接灭族就完了。唐无忧可是个有原则的人,她只杀了要退婚的未婚夫,和未婚夫勾搭害她的二姐,继母,大姐,大哥大师兄小师妹真是心那年我双手插兜,修仙后没有对手...
快穿钓系宿主撩翻神灵
简介关于快穿钓系宿主撩翻神灵纪宁栎单身二十三年,好不容易有看上眼的帅哥,却在关键时刻被系统绑定,从此踏上了挽救低分小世界之路。渡劫期修士把他圈在怀里轻哄乖徒儿,不离开好不好?高岭之花当众向他表白,单膝下跪宁宁,嫁给我好不好?星际第一指挥官庄重的抚摸他的手背宁宁,向伟大的母星宣誓,我会永远忠于你。某个神明宁宁。纪宁栎滚!新世界恶魔与人类,娱乐圈选秀,古代篇皇帝和小太监(假的),人鱼和鲛人,恋综。...
谢见微阮颜
谢见微阮颜谢见微阮颜阮颜谢见微阮颜谢见微...